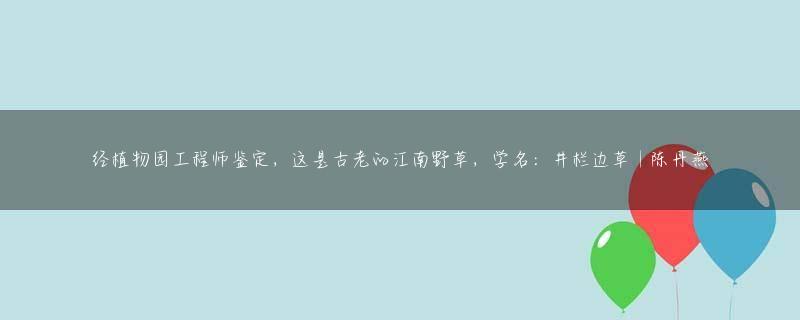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船公司在黄浦江边上的烂泥地上挖了一个船坞,用来修船,瑞镕船厂就此开张。德国战败后,这个船坞就易手给了英商。后来成为上海船舶修造厂,我小时候听到过这个名字,是因为父母先后到这个厂去劳动过。夏天时船厂高温,父亲回家时肩膀和手臂上都是通红的,而母亲有时回家来,要直接躺在走廊上的水泥地休息一下,然后才去厕所吐,她说自己中暑了。
等我自己看到这个船坞,已是拍摄《巡江记》的2021年了。从毛麻仓库外面的回廊望过去,船坞那边正在修整,听说有条古船要运过来,是从横沙岛那里的海底找到的,它很可能是从上海出发前往海外的商船。
等我终于走到船坞里去,已是2024年早春。那时候,船坞上已经造好了顶棚,古船已被海底淤泥团团封住,安坐于船坞底部,顶棚的注水系统每天定时喷洒纯水,维持古船在海底的环境,等待考古准备完成后,开船探宝。
然后,这个船坞和古船就会建造成古船博物馆,开放给公众。
这大概是我探访过的,与黄浦江航运的历史最相关的公共博物馆了。封住古船体的是湿滑的深灰色烂泥,覆盖在裸露木船舷上的,是密密麻麻的寄生物,贝壳、藤壶和小牡蛎,它们在深不见光的水下生长附着,外壳都是白色的。如今就是死了,肉体化没了,外壳还是牢牢吸附在船舷的木板上,不肯脱落。
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封在烂泥里的,除了古船和船上的货物,以及船员,还有船蛆。船蛆生活在木船的木头里,在坚硬的船木里不停地钻洞。它的寿命短,却繁殖力强,一代代的,就以在沉船的木头里钻洞为使命,从不懈怠。子子孙孙在水波里繁殖,找到水下的木头就进去打洞。而且分属细致,一种蛆是专门钻穿木板的,另一种是专吃掉木头的,还有一种也是,却因为长相不同,而叫了另一种名字。它们中的某一代应该也被封进了烂泥里,在古船里寿终正寝。我相信它们都是白色的,因为总是见不到光。从未想到它们像人一样有高有矮,高个子竟有1米8,比大多数江南的蟒蛇都长。我怕它。
除了大白条的船蛆,还有一种灰白色的蛀木水虱,它长得小,才2毫米,长得像蝉,肚子上长出许多细腿,带着个小细勾子,一副比蝉邪恶得多的样子。
还没见识到沉船里到底埋着什么宝贝,就先谈论了里面到底有什么虫活着。这就是我们在烂泥上一步一滑时说的话。
在一团烂泥上,我见到一瓣微小低矮的小草叶,只有我的指甲那么大小,活着,纤细,柔软。不知道它怎么能在这里长出来。而且是绿色的。
我很愿意相信,它是一粒草籽,长长久久埋藏在海底下,烂泥里,却没死。只是一直无法发芽,一直等到跟着烂泥离开海底,见到光的那一天。我很愿意相信它是古船偶尔带着的草籽,它的矮小和脆弱,都因为它来自一百多年前。我爱它,它就像一声来自那么深的水下,那么久的从前的问候,让人心突然就软了一下。
其实,在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的外滩公园那片滩地,最初也来源于一条沉船。沉船挡住了水道,也挡住了下游流动和堆积的泥沙,那种泥沙稠厚沉郁,渐渐形成了外滩的一小块滩涂。到了1860年,涨滩就能开垦出来做公园了。说起来,它是黄浦江边最早的公共空间,被称为public park,不到一公里。现在,黄浦江边的公共空间已经有45公里了。当外滩只有一条沉船上的小公园时,上海道台聂缉椝的理想是在公共空间里的环海联欢。现在,在黄浦江45公里的公共空间里,已经在准备一个向公众开放的沉船博物馆了。这个博物馆,用的是德商留下的船坞,清朝沉下的商船,纪念的是黄浦江的历史。
要是到博物馆开门时,这粒草籽能活着来迎接我们大家,会是多好的事。
覆盖着沉船的泥上长出的小野草,经过植物园工程师的鉴定,是古老的江南野草,学名:井栏边草。它被移送到辰山植物园培育,现在已经长得快40公分了。
作者:陈丹燕
文:陈丹燕 编辑: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 明
转载此文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