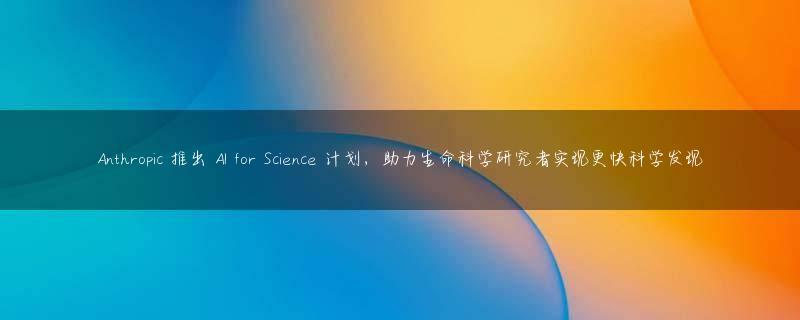2011年,物理学家们庆祝原子核发现100周年。1911年,在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位于曼彻斯特的实验室里,镭衰变释放出的一束带电粒子被射向了一片薄薄的金箔。人们当时普遍认为原子的大部分质量是平均分布的,就像布丁一样。如果是那样的话,镭发射的重带电粒子应该会穿过金箔,而且方向几乎不偏转。但是让卢瑟福吃惊的是,有些带电粒子直接从金箔上弹了回来,这表明它们被金原子中一些很小但很重的东西排斥。卢瑟福认为这是原子的核,电子绕着核像行星绕着太阳一样转动。
这是伟大的科学,但并不是所谓的大科学。卢瑟福的实验团队包括一个博士后和一个本科生。他们的工作仅仅从伦敦皇家学会得到了70英镑的资金支持。实验中用到的最昂贵的东西是镭样品,但是卢瑟福并不需要为此付钱——镭是从奥地利科学协会借来的。
核物理学迅速发展壮大了。在卢瑟福的实验中,镭发射的带电粒子没有足够的能量穿透金原子核的电斥力进入核本身。为了进入核内并了解核是什么,物理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了回旋加速器和其他可以将带电粒子加速到更高能量的设备。二战后,加速器的建设重新开始了,但是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目的。
物理学家在观测宇宙射线时发现了几种新的基本粒子。为了研究这种新物质,有必要人工大量制造这些粒子。为此,物理学家必须将成束的普通粒子,如质子(氢原子的核),加速到更高的能量,当质子撞击到静止目标上的原子时,它们的能量可能转化为新型粒子的质量。但这并不是为了创造最高能量加速器的纪录,甚至也不是为了收集越来越多的怪异类型的粒子(像兰花那样)。
建造这些加速器的目的在于,通过创造新类型的物质,了解支配一切形式物质的自然法则。尽管很多物理学家更喜欢卢瑟福那种风格的小型实验,但是发现的逻辑迫使物理学变得更大。
1959年,我作为博士后加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辐射实验室。当时伯克利分校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加速器——贝伐特朗质子加速器,它占据了校园中一座小山上的一座大型建筑。建设贝伐特朗质子加速器是为了将质子加速到足够高的能量来产生反质子。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反质子确实被制造了出来。但是令所有人惊奇的是,数百种新的高度不稳定的粒子也被制造了出来。新型粒子如此之多,以至不太可能都是基本粒子。我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知道基本粒子是什么意思。一切都令人困惑,又令人兴奋。
在此工作了10年后,已经很明显,我们需要新一代更高能量的加速器才能理解这些发现。这些新的加速器太大了,不能放进伯克利分校山上的实验室。其中很多甚至因为太大,不能由一所大学单独管理。但是如果这对于伯克利分校来说是一场危机的话,对物理学来说并不是。人们在各处建造了新的加速器,比如在芝加哥郊外的费米实验室、日内瓦附近的CERN(欧洲核子研究组织),以及美国和欧洲的其他实验室。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实验学家在这些实验室的工作,以及理论学家通过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的工作,已经帮助我们形成了一个全面的且已得到很好验证的粒子与力的理论,即标准模型。尽管标准模型很成功,但很明显,它并不是故事的结局。
一方面,这一理论中夸克的质量和轻子的质量到目前为止只能从实验中获得,而不能从某种基本原理推导出。我们盯着这些质量列表已经数十年了,感觉我们应该理解它们了,但是仍然完全不理解,就好像我们一直努力阅读的是一种用外语写下的铭文。况且,标准模型没能包括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比如万有引力以及暗物质,天文学家告诉我们,暗物质组成了宇宙中所有物质的5/6。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等待CERN的一个新加速器的结果,希望这个加速器可以让我们超越标准模型,再向前进一步。这个加速器就是LHC,它是一个周长17英里(1英里约为1609.3米)的地下环状设施,跨越了瑞士和法国边境。
在其中,两束质子被朝着相反的方向加速,每一束中的质子能量最终达到7TeV,即质子静止能量的7500倍。这些束在周围的几个观测站里进行碰撞,这些观测站里有和二战时的巡洋舰一样重的探测器,用于分析碰撞中产生的各种粒子。
我们希望,LHC的最激动人心的发现能带给我们一些惊喜。不论它是什么,很难看出它如何将我们一直带领到一个最终的、包含万有引力的理论。所以在下一个10年,物理学家们大概会请政府支持那个时候我们认为需要的某个新加速器。那将会是一个非常难推进的项目,我的悲观部分源于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另一座大型加速器争取资金的经历。
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开始计划建造SSC(超导超级对撞机),它会将质子加速到20TeV,是LHC所能达到的最高能量的3倍。经过10年的工作,设计完成了,地址选在了得克萨斯州,地已买好,并且开始建设隧道和使质子转向的磁铁。然而在1992年,众议院取消了对SSC的资金支持,随后两院协商委员会又决定恢复资金支持。但是第二年事情重演了,而这次众议院没有听协商委员会的。
在花费了近20亿美元、数千人一年的工时之后,SSC“死”了。有人说“杀死”SSC的是超支,但这并不属实。甚至有媒体中伤说,拨款也被用于购买行政大厅中的盆栽。预算确实增长了,但是原因之一在于,国会年年都没有按计划提供充足资金。这推迟了完工时间,因此需要的支出也就增加了。即便如此,SSC还是克服了所有技术挑战,其花费与LHC的不相上下,甚至其建设时间比LHC早了10年。
SSC的支出是1992年新当选的国会议员的靶子。他们热切地想要表明,他们能够切下他们眼中得克萨斯州的这块肥肉,并且也没觉得这有多么事关重大。冷战已经结束了,SSC的发现不会产生任何有实际价值的东西。在促进发明方面,大科学等效于技术的战争,而且它不会杀死任何人,但也没有人能预先承诺会有什么衍生品。
真正激励基本粒子物理学家的,是对世界秩序的一种感觉:他们相信,世界是由简单而普适的法则支配的,而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法则。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其重要性。
在关于SSC的论战期间,我和一位持反对意见的国会议员一起上了拉里·金(Larry King)的广播节目。这位议员说他并不反对把钱花在科学上,但我们必须设置优先级。我解释说,SSC将会帮助我们了解自然规律,我问这是否值得高优先级。我清楚地记得他的回答是“不”。真正激励立法议员们的,是他们选民的直接经济利益。大的实验室会为其附近社区带来工作机会和钱,所以它们可以吸引其所在州的立法者的支持,以及来自很多其他国会成员的冷漠或敌意。
另一个使SSC遇到挫折的原因是科学家之间对经费的竞争。在各个领域工作的科学家都会同意SSC将有助于科学工作,但是有些则认为这些钱在其他领域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比如他们自己所在的领域。时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是一位固体物理学家,他反对SSC,认为SSC的经费不如花在其他地方,比如固体物理学领域。
在基础物理学领域,即使不建设新一代加速器,也有其他工作可做:我们可以继续寻找罕见的过程,比如推测出的极慢的质子放射性衰变;在研究中微子的性质方面,也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我们还从天文学家那里获得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但是,如果不在高能领域的前沿推进,我不认为基础物理学可以获得重大的进步。所以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们可能看到对自然规律的探寻逐渐停滞,在我们有生之年也不会重新启动。资金支持在所有科学领域都是问题。过去1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能够支持的资金申请从33%降到了23%。而大科学又有其特殊问题,不能轻易缩小规模——建一个只有半圈的加速器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天文学的历史与物理学截然不同,但它遇到了很相似的问题。天文学很早就成了大科学,获得了来自政府的大量资金支持,因为它在某些方面非常有用,而物理学直到最近都没有什么用。在古代世界,天文学被用于地理测量、航海、定时以及日历制作,它也以占星术的形式出现,人们以为它可以预测未来。
政府建立了天文研究中心,包括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博物馆、9世纪巴格达的智慧宫、15世纪20年代乌鲁伯·别克在撒马尔罕建造的伟大的天文台、1576年丹麦国王赐予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一座岛以供他建设“天堡”,还有英格兰的格林尼治天文台以及后来的美国海军天文台。
但现在,天文学面临的任务超出了个人资源的范围。为了避免地球大气引起的图像模糊,也为了观测不能穿透大气层的辐射,我们不得不将天文台送到太空。通过卫星天文台(比如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探测器、哈勃太空望远镜等)与高级地基天文台的协同观测,宇宙学有了革命性的发展。
但是,就像基本粒子物理学停滞了数十年一样,宇宙学也面临停滞的危险。1998年,人们发现宇宙正在加速膨胀,这可以用各种理论解释,但我们没有能指向正确理论的观测结果。早期宇宙残留的微波辐射的观测证实了关于暴胀阶段的普遍看法,但是对于暴胀涉及的物理过程没有给出详细的信息。我们将需要新的卫星观测站,但是它们会得到资金支持吗?
计划作为哈勃望远镜后继者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其经历令人不安地回想起SSC。在奥巴马政府2011年要求的财政预算水平下,这一项目将会继续,但这点钱不够支持它被发射进入轨道。2012年7月,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投票决定完全取消韦伯望远镜。
有人抱怨说支出增加了,但是就像SSC一样,支出增加的一大原因是项目年复一年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最近,对于这一望远镜的资金支持恢复了,但是前景不容乐观。这一项目已经被排除在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任务指挥中心的计划之外。
韦伯项目的技术表现非常优异,而且已经花费了数十亿美元,SSC也是如此,却并没有让之免于被取消的命运。同时,在过去几年里,NASA对天体物理学的资金支持减少了。2010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进行了一项关于天文学在下一个10年发展机遇的调查,为新的太空天文台设定优先级。优先级最高的是WFIRST,一个红外巡天望远镜;下一个是“探索者”,一个中等大小天文台项目,规模类似WMAP(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然后是LISA,一座引力波天文台;最后是一个国际X射线天文台。但是预算中没有任何资金用于这些项目。
欧洲正在填补大科学领域的一些空白,比如LHC和卫星微波天文台普朗克。但是欧洲的财政问题比美国还严重,而且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将大型科学项目从欧盟的财政预算中移除。
国际空间站在SSC的取消中发挥了作用。1993年,这两项提案在国会进行了关键的表决。因为国际空间站的管理地点将设在休斯敦,二者都被看作得克萨斯州的项目。1993年,克林顿政府许诺支持SSC之后,又决定只能支持一个得克萨斯州的大型技术项目,并选择了空间站。
国会议员们对二者的区别并不清楚。在众议院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我听到一位国会议员说他能看出空间站会如何帮助我们了解宇宙,但不能理解SSC。我当时真想哭出来。空间站的巨大优势是它需要花费10倍于SSC的资金,所以NASA可以将开发它的合同分散到很多州。如果SSC耗资更多的话,它也许就不会被取消了。
大科学需要竞争政府的资金,对手不仅包括载人航天项目,还有各种科学项目,以及很多我们需要政府做的其他事情。我们在教育上的投入不够,不能让教师这一职业吸引我们最好的大学毕业生;我们的铁路客运线和网络服务,与欧洲和东亚比,相形见绌;我们没有足够的专利审查员来处理新专利的申请,结果是无休止的拖延;很多美国人没有得到足够的医疗保障;等等。实际上,在当前的国会,相比科学,政府的很多其他职责受到了更恶劣的对待。
我们最好不要通过攻击其他需求来捍卫科学。我们可能会输,而且也应当输。对我来说,真正需要的似乎不是为某一项或者另一项公众福利做更多的辩护,而是希望所有关心这些事情的人团结起来,恢复更高而且更激进的税率,尤其是对于投资收入。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和经济学家谈过,并了解到政府花的每一美元都比减税更能刺激经济。要说我们不能负担政府支出的增长,完全是谬论。但是,由于现在反税收狂热已经攫取了公众的注意力,这样的看法是政治毒药。这才是真正的危机,而且不仅是对于科学来说。
第三次沉思, [美]斯蒂芬·温伯格,中信出版集团 2021